





在雪域滋生、成长起来的藏传佛教,经过130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今天已发展成为世界佛教中经久不衰的一个流派。它不仅具备系统的佛学理论,规范的修持方法,而且囊括了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工艺、美术、语言学、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深深地扎根于藏族以及其他信奉藏传佛教民族大众的心间。
藏传佛教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许多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蒙古的社会组织中,“喇嘛”和“喇嘛庙”是两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藏传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蒙、藏两个民族情感及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自公元13世纪起,蒙古社会的上层与藏传佛教的首领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社会。
创建大元帝国的英雄忽必烈,尊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两代教主为国师,与他们商议治国和统一中华各民族的大业。并请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世祖八思巴为蒙古民族创制新字。最初在蒙古。民族中普遍使用的文字,就是藏传佛教高僧创制的“八思巴蒙文”。
到公元16世纪,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达汗励精图治,决心在蒙古地区大力推行藏传佛教,于公元1578年在青海仰华寺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举行盛大会晤,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几年后,达赖三世应邀亲临内蒙西部传教,并圆寂于此。三世达赖的灵童便转世于蒙古土默特贵族家庭——那就是第四世达赖云登嘉措。
由于历史上一系列的宗教事件和活动,使藏传佛教在蒙古中部、西部十分兴盛。曾住锡内蒙古的章嘉活佛和住锡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是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代理达赖喇嘛在内蒙、外蒙管理教务的呼图克图。许多藏族高僧和蒙古族喇嘛也在蒙古各地纷纷建寺传教,并把大量藏族文化带到了内蒙。
在蒙古草原上,藏传佛教的寺庙随处可见。人称“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渺渺召”。召,蒙语就是寺院的意思。仅在呼和浩特地区,就有大小召庙10多所。
在蒙古人的家庭中,也有送幼子去寺院当喇嘛习经修持的习惯。蒙古族群众在生活中遇到重大事情,也要请喇嘛念经,举行祈祷仪式。许多蒙古族佛教徒也把去拉萨朝圣看作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事情。正因为这样,不少蒙古家庭稍殷实一点,便花钱送自己的子弟到拉萨拜佛,有可能的话,还要让他们在西藏研究几年佛经。他们的虔诚,往往要经受遥遥路途和青藏高原稀薄空气的考验。
藏、蒙两个民族,虽一在北方,一在西南,但因共同信仰的关系,相互间一直保持了有如亲戚一般的亲密关系。
此外,位于藏区和与藏区社会发展相近似的10多个少数民族,也以藏传佛教为本民族的主要信仰。
位于甘肃西部的裕固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一般每个部落都有1个寺院,个别部落也有建2个寺院的。景耀寺、康隆寺、转轮寺、莲花寺、明海寺、长沟寺、红湾寺、水关寺、夹道寺等就是分属于不同部落的寺院。裕固族寺院的规模一般比较小,其内部组织不如藏区寺院那么严密,有的寺院有法台、喇嘛(或称堪布、活佛),有的寺院则只有僧官或提经。裕固族寺院的喇嘛僧人大部分都结婚,他们除宗教节日和放会时到寺院念经外,平日大都在家参加牧业劳动。其余如崇拜的神灵、祈祷方式、寺院礼仪、宗教节日等方面均与藏区无多少区别。
藏传佛教各派从公元11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地传播到了滇西北地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中甸县、维西县)、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兰坪县、福贡县、贡山县)以及丽江(丽江县和宁蒗县)等地区,长期以来对云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普米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形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主要分布在云南丽江、维西、贡山纳西族地区及德钦、中甸部分藏族地区,主要寺院有丽江的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和纳西县的来远寺、贡山县的普化寺;宁玛派在元、明两代时曾盛行于中甸、德钦、维西等地区,宁玛派寺院在这里大小共有19座,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承恩寺、英珠寺、托拉寺、白塔寺、云顶寺、折崩寺等;萨迦派对于云南的摩梭人和普米族有较大影响,主要分布于蒗蕖和永宁等上述两族居住区。主要寺院有:永宁格姆山下和萨迦寺。(该寺定额僧人500名,全系摩梭人和普米族僧人)、蒗蕖的萨迦寺、挖开萨迦寺等。
格鲁派约在公元15世纪传入云南。公元1580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接受云南丽江纳西族木土司的邀请到达康区的巴塘、理塘一代传教,并在当时属于木土司辖区的理塘主持建立了理塘寺。至清初,格鲁派在云南中甸、德钦、维西等地已具相当规模,并发展到宁蒗、永宁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格鲁派从传入之时起,就和当地的世俗统治阶级紧密联系,与当地封建土司政权相互依存,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寺院经济,进而发展成为该地区社会中独立的寺院集团势力,对云南各民族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藏传佛教的其它任何一派。云南格鲁派的主要寺院有:中甸归化寺、东竹林寺;德钦县德钦寺、红坡寺;宁蒗县扎美戈寺……等等。
在云南纳西族和普米族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凡自然灾害、患病、丧葬、出行、修房盖屋等,都要请僧人念经作法事。凡有男儿的家庭,也都要送1至2名男儿削发当喇嘛;多数家庭建有自己的小经堂,供家庭进行佛事活动之用。此外,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生子命名、宗教节日等方面亦都不同程度地受有藏传佛教的影响。
除蒙古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外,还有土族、门巴族、白族、傈僳族、羌族、阿昌族、怒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也都主要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这些民族中,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这些民族处于社会内部部落割据、外部有强大入侵势力压迫和威胁时,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它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对于统一内部、抵卸外辱、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繁衍,以及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都无容置疑地起过积极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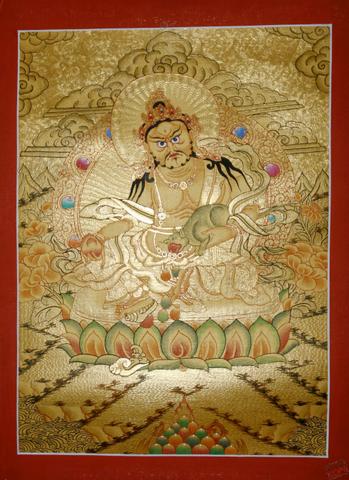



到了清光绪年间,他元1907年11月27日,清政府邀请十三世达赖赴五台山朝佛。11月29日,十三世达赖从塔尔寺启程,途经兰州、西安、临潼、华山,由潼关乘船渡黄河。1908年正月十八,达赖一行到达五台山麓。五台县官、五台山札萨、大喇嘛等在山门前扎下帐篷欢迎,一切礼节都按西藏的礼俗进行。
达赖在五台山给全体僧众讲经说法,摩顶。并派人给五台山各寺庙熬茶、发放布施。
公元1908年7月27日,清朝政府特派写机大臣和山西巡抚前来五台山,邀请达赖立即动身赴京陛见。十三世达赖即从五台山动身赴京,在春户(译音)地方改乘火车,于八月初三到达北京。达赖喇嘛至京后,在黄寺行宫休息。
八月二十日,达赖陛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九月初六,光绪皇帝在北京中南海设宴给达赖洗尘。
清政府册封达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赠送刺诱佛像和大量珠宝、绸缎。决定每年赏给达赖“廪讫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按时拨付。但十三世达赖在京居留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突然连续逝世。公元1908年十月初九日,宣统皇帝继位。达赖喇嘛提出了返藏要求,清朝政府批准达赖回藏,并给沿途各省下了命令,转饬所属州县,准备丰盛的招待派兵弁担任警卫……
从以上缀述可大略看出,藏传佛教对于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的政治发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
时至今日,经过一代又一代藏传佛教僧侣、信徒们的不懈努力,藏传佛教已越出国界在全世界许多地区也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今天,藏传佛教的信徒除分布于西藏、内蒙全境、川西北、青海大部,甘肃南部,新疆准噶尔盆地,云南丽江以北各县,宁夏北部,辽宁与黑龙江两省西部外,还分布于外蒙古、原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地区、与西藏接壤的不丹、锡金、孟加拉、尼泊尔、以及印藏交界外的广大地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藏传佛教也在欧美传播很广。比如:
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矗立着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乌金贡桑确林寺;
在希腊的雅典附近,每年从各地来此学习藏传佛教宁玛派教法的学生达几百人;
在法国南郊的卡斯特朗市,也建立了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藏传佛教的噶举派,自1959年以后在国外的活动也增多了。目前在印度、尼泊尔、不丹、共有24座寺院,1000多僧尼。此外在加拿大、法国、英国、美国、锡金、拉达克也有零星的寺院。
……关于藏传佛教最近一个时期在欧美广泛传播的原因,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谭·戈伦夫在他题为《北美藏学研究简介》的讲稿中,作了如下分析:“随着六十年代初,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发生,欧州和北美的青年人对东亚的兴趣也相应增长起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就如同对美国文明失望的青年人到印度去寻找宗教出路一样,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整个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这个时期,数以万计的西方人士涌入印度和尼泊尔,对于自己国家文化相去甚远的这一地区的文明产生了好奇心;宗教的信徒,虔诚的和非虔诚的,也从北美和欧州大批地会集到这里……美国人的兴趣从欧州转向亚洲和宗教徒涌入南亚这两个因素,为西方人士改变原来信仰而信奉西藏佛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的确,北美洲的不少人由于对藏传佛教和西藏事件所吸引,在这一地区无形中形成了“达摩中心”。这些中心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卡瓦钦达摩中心和夏威夷巴哈拉的德拉昂字,穿越大陆扩展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由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徒降央仲巴仁波且在一所大学里设立了“那若巴学院”,这个中心对藏传佛教的教义进行专门研究.降央仲巴仁波且还在北美的纽约、迈阿密、华盛顿、洛杉矾、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亚特兰大、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等地创办了4个“金刚界”学院和24个“法性”中心,同时这些机构也就构成了广布于北美的出版网。
在美国还有由宁玛派僧人德江仁波且创办的“益西宁波”(即智藏论师、古印度佛学家)中心,在美国各地有6个活动中心。
这些纯粹的宗教组织,主要研究、宣传藏传佛教的教义,出版关于藏传佛教的翻译作品。
1958年以后,由瑞士尼姑阿尼安塞美特发起成立了一个“高级西藏学研究中心”。此后,类似的西藏研究中心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成立了许多。目前,西藏学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门学科。
在北美,有从事西藏研究的高级学术机构21个。如由格西·泽登降称建立的洛杉矶“东方研究大学”;科罗拉多州博拉德的“那若巴学院”;马塞诸塞州阿墨斯特的“美国佛学院”;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宁玛学院”……等等。
纽约的“西藏研究中心”开办西藏佛学、语言、坐掸、烹任等讲习班;
加拿大的“艾伯塔西藏社”举办宗教、语言学习班;
此外在北美的新墨西哥圣菲、印弟安那大学也都设有西藏佛教研究中心。
在原苏联,藏学、西藏佛教跟远东问题、布里亚特、蒙古问题一样,从18世纪开始为原苏联科学界所重视。在沙皇和苏维埃时期,出现了一批研究西藏问题的著名专家。1917年于彼得堡建立的佛教文化研究所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研究西藏问题中心,这个机构的研究文章多系佛教哲学论文,它所提供的有关西藏问题研究的资金、档案、文物和图书,其规模和数量为少数国家所能及。此外,在原苏联的科学院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研究所、亚洲博物馆、喀山大学、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东方学系、符拉迪活斯托克东方学院、苏联地理学会……等都设有从事西藏问题研究的单位。
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某些研究机构,自20年代和30年代时就对中亚问题越来越感兴趣,成立了“莱比锡大学比较宗教史研究所”。该校的约翰、舒伯特于1960年获得第一个藏学教授职位,他从中国资料中研究“多种语言的喇嘛教铭文”、开设了“西藏历史学家”这门课程。
日本于1953年成立了西藏研究会(JATIS),不少学者致力于藏学和藏传佛教的专门研究,1961年,3名藏族人索南伽、开珠藏卜、才仁根玛来到日本,参加东京的东洋文库工作,开辟了日本藏学研究的新纪元。由于在日本的藏人与日本学者通力合作,大大促进了藏学的研究和出版工作。
在法国,由于早期学者巴考、吉博、利奥塔尔、达维、蓓萨尔等对西藏的考察记录以及相当数量的普及读物的发表,使不少法国人对西藏和西藏佛教产生兴趣。而女藏学专家拉露于30年代编写了大藏经《丹珠尔》索引,更为法国学者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起了分类、编目的作用。
在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也都有佛教的传播和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在匈牙利科学院中,收藏着浩繁的藏文、蒙文书籍,这为顺利地研究藏传佛教铺平了道路。在布达佩斯,收藏有《甘珠尔》和《丹珠尔》。在那里,一些翻译的藏传佛教典籍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
此外,在缅甸、印尼、印度、意大利、德国(指原联邦德国)、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已先后召开过有关藏学的国际会议。藏传佛教正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甚至信奉。
50年代末,大批旅居海外的藏族同胞把藏传佛教寺庙也建在了旅外藏胞比较集中的居住地。在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家,建立起藏传佛教寺庙145座。分散旅居的藏胞,大多依然在住宅中设有佛堂和佛龛。他们身处异国它邦,仍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宗教活动。祈祷众生平安、祈祷生活幸福。
有一位由美国回故乡——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定居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贡保才旦,他年轻时曾是夏河县红教寺的喇嘛,1957年去印度朝圣,在印度居住了20年。后来又旅居美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州讲经传法。他在美国有60多名弟子,其余听他传经讲课者不计其数,他们来自全国各地。1984年贡保才旦喇嘛由于思乡心切而回国定居,但他那些在国外的弟子和欧美各地的信徒,仍追随着他,千里迢迢从海外来向他拜师求教。共同的信仰,将异国的师徒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外国弟子与这位中国藏族高僧结成了令人感动的深厚友谊。
除了一些前来中国拜师学徒的信徒外,每年前来中国瞻礼和研究藏传佛教寺庙、文物的外国学者、宾朋也随中国改革开放而逐年增多。前去西藏、青海、甘肃甘南、四川甘孜、阿坝、云南西部参观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作为佛教中一个重要支系,已受到世人的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