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简 介 前 言 展出作品 时间地址 相关文章 展览空间 展览图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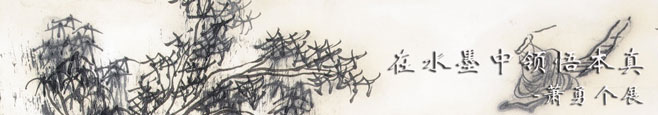 |
| 萧勇,在水墨中领悟本真(大师的传承者) |
令人目光惊异的批评文字往往从偏僻处开始,在人们忽略或已丧失关注能力的地带发问,劈开习俗的遮蔽,让事情得以显露本真。中国艺术批评正处于这一被期待状态。 其实,中国画创作已先于批评而被纳入这一期待之中了。但期待毕竟公示了被期待者尚未在场,它仅是作为可能出场者被有所期待。所以,我们将这种期待折回到中国画现存秩序中那些未被披露的欠缺的地带,才可明了此一期待之必要。 谁在此欠缺的地带逗留、沉思呢? 沉思的道路总是深度追问的道路。中国画作为中国艺术精神最基础的那种力量是否正被败坏?中国画家们是否已成为隐秘转动的庞大消费机器中一个个配件?事实上,大部分中国画家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某种事件的参与者,并在这一进程中泥沙俱下。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笔墨大都俱已在以技术为主导的消费时代被赤裸裸的工具化了。另有部分自称为坚守者的画家,依偎在传统的怀抱中作未成年状态的弱不经风的纸面抒情。置身此种境遇,我们可以追问这一系谱最初的可疑,由此,或可在对所谓“情调”、“境界”之类美学概念的解读中,找到批判性认知和领会的新的话语空间。在我们面对什么有待我们去追问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具体地回到思者当如何去思的问题上来,学会思,实质上有时比思什么更为重要。(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 有了如上的提示,我们在此尝试和本文读者踏在同一条去蔽的路上,首先,从欠缺这个词出发,前面提及的中国艺术精神中最基础的那种力量,并非如人们假定的那样是一种圆满的力量,它只是仍然有待生发的力量而已。另一方面,欠缺不仅是指中国画传统中有什么艺术意愿尚未完成,欠缺本身便是对创造的吁请,它可以直接指示某种力量的根本性缺席,这种力量在中国艺术传统中,从未在场过(很少有人相信,就传统而言,已有什么在欠缺处覆水难收了,并终止于这一欠缺地带)。我们所说的欠缺总是与出口、出路有关,凡欠缺、断裂处皆可被视为开端。如是,艺术家们或可拥有绝地逢生的可能。 但对这种有点捉摸不定的可能,绝非仅凭一点才情便可从容把握了。艺术家们要尝试舍弃那些已成负担的陈芝麻烂谷子,在对存在和事物秩序的再度倾听和领悟中,与存在的可能性直接照面。从中国画的现状看,寄生在看似稳定的结构中的一些画家们,服从于这个结构给定的秩序,差异和不确定性总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尚未领悟到,可能所以可能,正是差异和不确定性力量使之可能,这也是可能这个词在当下境遇中和我们相遇的意义所在。而有创造倾向的艺术家,则在对差异和不确定性的认领中目光锋利,去蔽者一旦从所蔽处脱身而出,笔墨也具有发问的力量。 画家萧勇正致力于在此开辟前行的道路。 萧勇,中国新文人画开辟性画家董欣宾众多弟子中行为最为奇诡者。他早年出入往返于董门,心思却在意识形态上,他对存在的境遇有过大部分中国画家们不曾有过的关注,入世变革之精神迄今仍在。绘画这一笔墨之事,一度曾被萧勇称之为文人自隐自喻之偏窄小道。受挫后顿悟艺术之为艺术乃是坚守本真不断开启、去蔽的一种创造。是短暂者得以诗意地存在于世并有所承担的天命的一部分。有此认识,萧勇回转到艺术之路,一出场便与众不同。当画家们正不假思索地沉湎于画法自然这类老生常谈时,萧勇在发问,这个在艺术理论中早已被前置的自然意指什么?是肉眼所及的山水风物吗?当自然这个词被领悟为生发中自在自为的不断敞开者,艺术本身就是内在于这一敞开过程中最本真的力量,如此,自然与艺术原初便气血贯通,自然并不是在艺术之外的一个对象,自然这个词在精神层面的力量只有艺术才可诗意地披露。艺术之为艺术,中国画之为中国画也将深深契合于这一领悟。中国新文人画的杰出画家董欣宾对此也曾有所颖悟,他在对传统的追问中探索中国画发展的可能和出路,他开合大度,倾重于线的率性生发,并独具匠心的将中国线条的形式力发挥到当下几乎无人并论的高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并左右了中国新文人画的发展方向。受其影响至深的门人笔者大都认识,董欣宾的线条形式对这些门人来说几乎已入骨在身,那些有别于前人亦文亦野的线条在画面上的极致运动形态,在当代绘画史上自有其不可置疑的夺目的艺术位置。但这些对萧勇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他所承继的是董欣宾艺术精神中最具生命力的那一部分,大师的光芒强烈,往往使邻近者不见其光源所在,当弟子们分享某种荣耀的同时,目光迷漓者很可能被这种光芒笼罩,从此成为不知所往的游魂。 没有欠缺的大师是不存在的。而大师们的欠缺往往是遮蔽更深处的一种欠缺。 萧勇警惕兮兮,每日自问于水墨世界。他开始从传统到董欣宾直面逼问线的时间线,由线条构成的画面形式是不是一种主客二元符号的对应?内在于其中的结构是否仍属于一个自闭型稳定态结构呢?从笔墨入手,他更倾向于线条之间的相互生发,倾向于一个互动敞开型结构的初创,在消解传统隐性权利符号的同时,使差异性得以在画面成为水墨秩序中一种不被轻率整合的在场力量。应该说,对中国画结构的这一深度发问,使中国画作为视觉艺术原先的基础变得可疑起来,这已逾越了其师董欣宾曾对结构的艺术理解,从而将画家的艺术视野扩展到一个汉语思想未曾真正到达的陌生区域。 一个艺术家在视觉艺术认知上的自觉,也可能使其在转变期比别的画家落笔时有更多的迟疑,由此认知上的自觉达至作品真正的别开生面,往往是一条并不那么容易展开的披荆之路,艺术要求画家从观念世界回到微妙的笔墨感觉中来,它有赖于与技法相融的创造性实践。到得心应手处,作品才会光芒逼人。 萧勇近期的水墨作品已在此转换生发中,仅就其作品在倾斜状态中给出的预示,便让人们的期待拥有了并不寻常的价值。 |
| Copyright Reserved 2007-2019 中国艺术品收藏网 版权所有 |